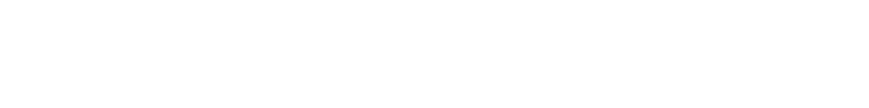楊某于2009年11月27日入職某公司從事保潔工作,雙方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公司未為楊某繳納醫療等社會保險費。楊某于2013年1月起在戶籍地自行繳費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后與城鎮居民醫保整合為城鄉居民醫保)。
楊某患病前月平均工資為2801.67元。2015年6月29日,楊某以膝蓋疾病導致下肢癱瘓為由,向公司請假至同年7月20日。7月18日楊某向部門主管發短信繼續請假,公司確認收到短信。同年7月24日,公司以楊某“自動離職”為由解除勞動關系。楊某自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2月16日在多個醫療機構治療,產生醫療費共計65632.08元。雙方確認楊某上班至2015年6月28日。
楊某申請勞動仲裁,后不服裁決結果,訴至法院,要求增加支付醫療期間工資、醫療補助費、醫療費損失賠償等。
圖片
探討
1.在職工已經參加居民醫保的情形下,用人單位能否為職工辦理參加職工醫保手續、補繳職工醫保費用?
2.在職工已經參加居民醫保、用人單位未為職工辦理參加職工醫保手續的情形下,勞動者是否存在醫保待遇損失?勞動者如何為這一損失尋求救濟?
3.用人單位未為職工辦理參加職工醫保、職工參加居民醫保的現象如何規制?
法律名詞解釋
醫療期:
根據《企業職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規定》,醫療期是指企業職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負傷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勞動合同的時限。
根據本人實際參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單位工作年限,給予3個月到24個月的醫療期:(1)實際工作年限10年以下的:在本單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為3個月;五年以上的為6個月。(2)實際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在本單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為6個月;5年以上10年以下的為9個月;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為12個月;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為18個月;20年以上的為24個月。
審判
2016年12月21日,一審法院民事判決:確認楊某與公司之間勞動關系已經解除;公司須向楊某支付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金33620.04元,支付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24日期間病假工資1047元,并駁回楊某其他訴訟請求。楊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維持原判。經檢察機關抗訴,2021年5月10日,所在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再審民事判決,維持一、二審部分判決,增加判決公司向楊某支付2015年6月29日至2016年3月28日(9個月醫療期)期間病假工資10872元;支付醫療補助費16810.02元及鑒定費用2212元;支付醫療費報銷差額損失9954.77元。
圖片
關于醫療保險報銷差額問題,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以下簡稱《社會保險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醫療保險,繳納醫療保險費”之規定,用人單位違反此規定應向勞動者賠償因未為其辦理社會保險手續,且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能補辦導致其無法享受社會保險待遇而遭受的損失。楊某主張的本可享受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待遇與其已享受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待遇之間的報銷差額,屬于因公司未為其辦理社會保險手續所遭受的損失,再審予以支持。
評析
本案與醫保關聯的問題是,用人單位未依法為職工辦理參加職工醫保手續,職工參加居民醫保時的損失如何有效進行法律救濟。如何彌補勞動者的損失并進行更為全面的救濟,不僅事關勞動者的社保權益,也事關社保制度的可持續發展。
一、職工不當參加居民醫保,能否補辦職工醫保并享受相應待遇
無可爭辯的基本事實是,在該案中,用人單位應當為楊某辦理參加職工醫保手續而不辦理,屬于違法行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法釋〔2020〕26號)第一條第(五)項規定:勞動者以用人單位未為其辦理社會保險手續,且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能補辦導致其無法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為由,要求用人單位賠償損失發生的糾紛,屬于勞動爭議,當事人不服勞動爭議仲裁機構作出的裁決,依法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據此,勞動者主張用人單位賠償職工醫保待遇損失,必須以不能補辦職工醫保而導致職工醫保待遇損失為前提。本案是否符合這一前提條件,法院未作具體分析。楊某應當參加職工醫保但未參加,不應當參加居民醫保卻參加了居民醫保,在此情形下是否可以補辦職工醫保手續存在爭議。但即便補辦職工醫保,楊某亦不能享受職工醫保待遇,這當屬無疑:楊某不僅在醫療事實發生前未參加職工醫保,且未參加職工醫保的時間過長。
圖片
二、勞動者對用人單位未辦理
職工醫保手續的
賠償請求權及基礎
上述司法解釋僅規定類似情形屬于法院勞動爭議案件管轄范圍,并未給出支持勞動者損失賠償請求的具體法律依據。《社會保險法》規定了用人單位的強制性繳費義務以及未依法繳費的法律責任,但未規定用人單位違反強制性繳費義務時勞動者的醫保待遇等權益如何保障。上述司法解釋主要是程序性規定,雖然在實踐中法院一旦受理只要事實成立就會支持勞動者的索賠請求,但畢竟沒有給出實體法的明確規定。
目前,勞動者對用人單位未辦理職工醫保手續的賠償請求權主要是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即“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用人單位違反強制性法律規定未給勞動者辦理參加職工醫保手續,存在過錯;勞動者無法享受職工醫保待遇,存在損害;勞動者的這一損害與用人單位的過錯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因此,侵權責任成立,用人單位應當承擔損失賠償等法律責任。雖然司法實踐沒有列明勞動者要求用人單位賠償醫療保險報銷損失的請求權基礎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但其實質運用了這一原理。
三、用人單位應承擔職工醫保的全部報銷金額還是差額補償
楊某未參加職工醫保,職工醫保基金不會報銷楊某的任何醫療費用;同時,楊某享受了居民醫保待遇。職工醫保與居民醫保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兩者待遇存在差距。用人單位應承擔職工醫保的全部報銷金額還是職工醫保與居民醫保的待遇差額,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本案法院支持了差額補償,基于侵權損害的填補原則,這一做法是可取的。
由于用人單位承擔的是侵權損害賠償責任,需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的損害填補原則。因為用人單位未依法參加職工醫保,楊某產生的損失就是其如果參加職工醫保應當由職工醫保基金支付的金額,該損失應當由侵權人即用人單位承擔;如果受害人獲得超過其損失的賠償,則屬于不當得利,違背了任何人不得因為違法行為而獲利的公平原則和基本倫理。在本案中,楊某已經獲得了居民醫保的給付,其醫療費應報銷金額已經獲得了部分填補,如果再獲得相當于職工醫保基金全額支付的金額,則意味著不僅個人損害獲得填補,還獲得了收益,這有違法理。
四、應參加職工醫保而參加居民醫保情形的規制
本案情形還存在一個根本性問題,即用人單位是否應為楊某補辦職工醫保手續并補繳職工醫保費用?本案作為勞動爭議訴訟,法院未考慮且未處理該問題,是正當的。但從問題的整體解決上來看,默認此種情形下勞動者可以參加居民醫保,用人單位得以逃脫參加職工醫保的強制性法律義務并不妥當。這不僅損害了《社會保險法》等法律法規的尊嚴,也違背了“違法必究”的法治理念。但在實踐中,存在操作上的困境——即便養老保險費和醫療保險費不予補繳,但工傷保險費和失業保險費仍可能需要補繳,兩者會存在沖突。
首先,基于社會保險的唯一性理論,楊某不能同時參加職工醫保和居民醫保,因此在楊某已經參加居民醫保的情形下,無法為楊某辦理職工醫保的補繳手續。
其次,在現行法律體系下,用人單位違反強制性法律義務未給職工辦理職工醫保等社會保險參保手續,應予以糾正,即取消職工的居民醫保而將其納入職工醫保,或者直接將居民醫保轉變為職工醫保。
再次,由于職工已經參加居民醫保,特別是在參加居民醫保期間已經發生醫療費用,其對獲得居民醫保基金給付產生信賴,應當保證其獲得居民醫保的給付。從此視角考慮,采取將其居民醫保轉換為職工醫保、由用人單位補繳繳費差額的措施較為妥當,這樣不會影響職工已發生醫保待遇的享受。(ZGYB202508)
作者|向春華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